
周潔茹2015年香港西貢留影
內(nèi)容摘要:70後小説家周潔茹于上世紀90年代聲名鵲起,停筆十年的她重新回歸小説創(chuàng)作,近年的短篇小説更是呈現(xiàn)紛繁的面相:香港故事與女性經(jīng)驗交疊出現(xiàn),在地理空間意象、他者視角、女性經(jīng)驗的在場與權(quán)利話語的缺席等方面,具有深刻的啟發(fā)意義。本文試從“香港故事”和“女性經(jīng)驗”的創(chuàng)作譜係出發(fā),論述周潔茹近年短篇小説創(chuàng)作的敘事範(fàn)式、審美內(nèi)涵與思想價值。
關(guān)鍵詞:周潔茹;小説;香港;女性;敘事
用“回歸”來概括周潔茹和她的小説再恰切不過。1991年,中國的“新生代”女作家集體嶄露頭角的年代,1976年出生的周潔茹在《人民文學(xué)》《收穫》《鍾山》《花城》等重要文學(xué)期刊發(fā)表作品。1996至1998年,周潔茹的創(chuàng)作呈“井噴”狀態(tài),她發(fā)表的作品總計百餘萬字。對一個年輕寫作者而言,如此成績意味著,只要繼續(xù)創(chuàng)作和發(fā)表,就能逐步奠定在文壇的“江湖地位”。然而周潔茹並沒有循著這道軌跡走下去。1999年,成為專業(yè)作家的周潔茹開始寫她的第一部長篇《小妖的網(wǎng)》。十幾年後,“歸來”的小説家周潔茹在《十年不創(chuàng)作談》中警惕地自嘲:“很多時候,專業(yè)作家的位置會毀了一個作家,因為專業(yè)作家太幸福了,專業(yè)作家不用坐班,專業(yè)作家可以睡懶覺,專業(yè)作家被尊重,專業(yè)作家是行政編制……專業(yè)作家一百年沒有新作也沒有關(guān)係,因為你已經(jīng)是一個專業(yè)作家了。”這種“幸福感”令周潔茹感到了危機。2000年,24歲的周潔茹離開中國去了美國,這年是她生命的轉(zhuǎn)捩點和創(chuàng)作的分水嶺。此後她的寫作處在不穩(wěn)定的狀態(tài),直到移居香港七年,才又重拾小説,清理此前動蕩的人生。
2000年至今,周潔茹在《人民文學(xué)》《上海文學(xué)》《北京文學(xué)》《山花》《天涯》等刊物發(fā)表的小説,加起來不過二十篇;2013年以後刊發(fā)的小説佔了總發(fā)表數(shù)的一半。這批作品大體分兩類,一類是“香港故事”:以書寫異鄉(xiāng)人在香港的生活經(jīng)驗為主,計有《到香港去》《旺角》《鄰居》(原名為《新界》)《尖東以東》等,它們基本以香港“地名”為題目。《鄰居》尤其值得注意,小説原名《新界》(沿用“香港地名”的命名套路),其內(nèi)在刻畫和敘述的,仍舊是香港逼仄的公寓樓、人情、世態(tài),聚焦的仍舊是活生生的香港經(jīng)驗;另一類小説,筆者稱之為“女性故事”,計有《幸福》《生病》《結(jié)婚》《離婚》等,都與女性生命攸關(guān),一起一落,大開大闔,寫現(xiàn)代女性的生存體驗與精神疼痛。筆者借助這兩批小説來剖析周潔茹的創(chuàng)作範(fàn)疇與敘事特徵。
一.香港故事:地理空間與他者視角
周潔茹的香港故事——從《到香港去》,再到《鄰居》《旺角》《尖東以東》——勾勒出陌生化視角下的香港。這批“香港小説”,有著與葛亮的“香港主題”小説集《浣熊》不同的韻味。葛亮以“新港人”身份,力圖摘除其異鄉(xiāng)人特徵,用本土(對話中粵語的使用、對香港民間習(xí)俗的洞察等)的方式臨摹塵世男女的香港故事;他的小説與劉以鬯、西西、也斯、黃碧雲(yún)、董啟章等香港本土作家一起構(gòu)成鮮亮的風(fēng)景線。倘若沿著這道軌跡將周潔茹的香港故事也納入此範(fàn)疇,我們會發(fā)現(xiàn),這樣的流派劃分顯得生硬和牽強。在“新世紀香港小説趨勢”研討會上,周潔茹的發(fā)言袒露出其尷尬的“香港身份”:“所有除我之外的新來港人士,都是在第一個月就學(xué)會廣東話了。因為要融入香港社會,做新香港人。而不是像我這樣,時刻準備著,要離開香港。不會廣東話,是我的遺憾,要不然我就可以用廣東話的模式來寫我的香港小説,讓它們成為最香港的小説。”這裡的廣東話(粵語)與“最香港的小説”之間有著某種吊詭關(guān)係。她的“聲明”和香港故事形成奇特對照。換言之,周潔茹沒有使用粵語來寫有關(guān)香港的小説,但並不代表她無法呈現(xiàn)真實或者是“另類”的香港。很明顯,在周潔茹的語境中,“最香港”這一定語是需要被重新打量的。
什麼是“香港小説”?是否故事發(fā)生在香港,就可以宣稱自己歸屬這個概念?難道只有香港本土作家才能寫出地道的“港味”小説嗎?周潔茹的小説是對“香港小説”的反詰與逆寫,是對“香港”這一主體意識的顛倒。周潔茹用其鮮明的“自傳性”筆調(diào)(即便套上第三人稱的虛擬外衣,骨子裏依舊透著“我”説話的聲音)來寫香港。先看她寫于2013年的《到香港去》:內(nèi)地婦女張英為了給孩子買安全的奶粉,積攢假期,隻身跟了旅遊團赴港,整篇小説借用的就是張英的“遊客”視角,周潔茹讓這位第一次到香港的女人跟著旅行團遊歷香港:港鐵、金舖、星光大道、藥店等構(gòu)成了香港的都市符號景觀。在這篇小説中,張英從“渴望”去香港,到最後“不想”去香港——“張英忽然恍惚,不知道自己是為了什麼來。”她經(jīng)歷的是內(nèi)與外,自我與他者的隔膜和衝突。周潔茹用第三人稱呈現(xiàn)一個陌生化的,“遊客視角”下的香港,並非簡單的二元對立,其間還有夾雜著張英與內(nèi)地遊客的微妙關(guān)係:旅行結(jié)束過關(guān)時,張英被攔了下來,因為沒人告訴她,每人只能攜兩罐奶粉出境,而張英買了四罐。這篇小説寫得克制,沒有故作姿態(tài)的批判和申訴。張英成了無數(shù)內(nèi)地遊客的縮影,她是短暫徘徊于港地的一縷幽魂。“到香港去”作為述行詞已經(jīng)構(gòu)成香港小説詭異的地理空間符號。
再看《鄰居》,故事發(fā)生在新界的公寓樓裏。小説由“我”的夢境寫起,敘説“我”鄰居一對夫妻的故事。但其敘述筆調(diào)始終是隔閡和冷漠的。“我”經(jīng)常聽見女人高聲尖叫,飽受干擾的“我”叫來保安查看,直到他們搬家,“我”也只與這對夫婦打過幾次照面;小説的另一面,是“我”的朋友格蕾絲和她鄰居的故事。在“我”的鄰居搬走,新鄰居還未入住的間隙,格蕾絲家對面屋苑有對中年夫婦吸嗅乙醚死於家中。《新界》寫得鬼魅叢生,“不確定敘事”的手法頗有意味:對面屋苑夫婦的死,是“我”的鄰居夫妻的某種“對位”。《新界》故意混淆真假:是否自殺的夫婦,就是這對神秘的、矛盾滋生的夫婦的另一種結(jié)局?周潔茹的第一人稱令讀者感同身受的同時又拉開了距離,這是敘述的奇妙之處,看似彌合,實則裂隙已生。這是陌生城市的“陌生化視角”。在這裡,女性居住的房子,以及陌生的“鄰居”關(guān)係,成了一個地理空間和精神性場所,它是符號也是指涉對象——周潔茹用房子這件“容器”來盛放女性個體經(jīng)驗和香港這座“孤島”間的複雜關(guān)係。敘述者“我”帶著“窺視”的姿勢,勾勒出現(xiàn)代社會的“鄰居”群體:他們一直在,又一直不在,他們始終是陌生人。
在周潔茹的香港故事中,《旺角》顯得很獨特,作者用第三人稱講述“她”與一個香港警察的“偷情”故事,浮世的男歡女愛被賦予了另類色調(diào)。與警察分手後,“她”又格外想念他。在警察執(zhí)勤的旺角一帶他們相遇了,“她扭頭望去,只看見他的背,他真是不能與她相認,偷情的男女,旺角的街頭,陌生人一樣的錯過。”從私人的居住空間(《鄰居》)到公共場所(《旺角》),旺角提供給讀者的不單是故事發(fā)生的空間,還帶有隱喻和指向性,《旺角》中的“她”,無意間闖入香港居民的“佔中”運動(西方媒體稱為“雨傘革命”),而至始自終,“她”對警察、街頭帳篷、靜坐者(躲在帳篷裏吃麵的人)所構(gòu)成的強有力的政治景觀都是陌生的:小説出現(xiàn)“她不明白”,第一次是“她不明白他們?yōu)槭颤N在這裡”,第二次是,“她不明白她為什麼在這裡”。前者的“他們”指的是維持秩序的警察,第二個“她”,當(dāng)然就是小説的主人公了。換言之,小説寫的雖是男女情事,一旦放置於政治運動、公民抗議的背景中,其反諷的意味就出來了,游離的、漠然的女主人公,對香港的社會政治景觀的感受,與《到香港去》的“遊客視角”異曲同工。
《尖東以東》,講的是“我”的朋友周貓貓和他丈夫來香港旅遊,“我”帶他們逛街的故事。敘述者“我”退居故事角落,勾勒的出八零後周貓貓與九零後老公的婚姻悲劇。八零後的周貓貓是愛貓人士和環(huán)保主義者,相比之下,她老公卻喜歡和他的富二代朋友混在一起,思想幼稚、不思進取,是個不折不扣的拜物教信徒,小説的結(jié)尾,“我”不無諷刺地回憶道:“周貓貓的老公戴著那塊不知道真假也不知道值多少錢的手錶,對我説,我要做團委書記。我終於笑了出來。”他們的“離婚”是必然,背後掩藏著價值體系的崩裂。周貓貓的拜物教丈夫,其實是無數(shù)中國大陸的“土豪”和“暴發(fā)戶”的縮影,他們只關(guān)心名錶的真假、限量版球鞋的希貴,他們對香港的認知還停留在購物天堂、資本主義社會的淺陋層面,對這座城市發(fā)生的政治氣候的演變漠不關(guān)心,他們的精神早已被消費主義侵蝕一空。
以上四則“香港故事”,兩篇使用第三人稱(《到香港去》《旺角》),兩篇第一人稱(《鄰居》《尖東以東》),然而它們內(nèi)在的精神指向是相通的,它們描摹出在港的“我”與來港的“她/他們”的眾生相,來港的“他者”與在港的“我”互為鏡像,映照出陌生化視角下獨特的香港社會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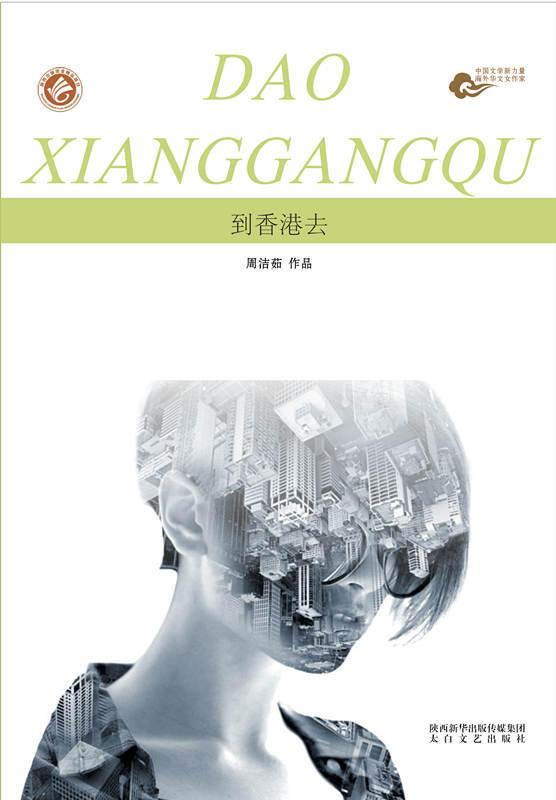
二.女性故事:經(jīng)驗“在場”與話語“缺席”
從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婚姻悲劇,到易卜生《玩偶之家》娜拉的出走,再到魯迅筆下《娜拉走後怎樣?》,在中西方文學(xué)史上,女性的地位問題、女性與男權(quán)社會及父權(quán)制的角逐較量一直是作家書寫的重心。周潔茹也不例外,她的四則短篇小説(《結(jié)婚》《離婚》《幸福》《生病》)寫的都是女性的生存疼痛和生命體驗。這批小説聚焦女性經(jīng)驗的在場和話語的缺席,散發(fā)著濃厚的“女性主義”色彩。
這批小説單就題目而言是頗值得玩味的,“結(jié)婚”與“離婚”對應(yīng),“幸福”與“生病”對應(yīng)。先看《結(jié)婚》,小説篇幅不長,類似“場景速寫”,其主要場景只有一個:“婚禮”,而且是非常特殊的婚禮。“我”的朋友張英要結(jié)婚了,可“我”卻直到婚禮前一小時才被告知婚禮改了地點。直到我“我”趕赴現(xiàn)場才一層一層剝開故事的迷霧。原來張英結(jié)婚,男方是再婚。婚禮現(xiàn)場,男方的前妻帶著兒女來鬧場,鬧到最後警察也來了,婚禮沒有辦成。小説的結(jié)尾是一齣荒唐的鬧劇:大家圍坐一桌,無力地“吃飯”;而在《離婚》中,周潔茹講述的是“我”與三個閨蜜:米亞、飄飄、小奇各自的婚姻故事。小説開篇寫四個閨蜜到寺廟裏找和尚算命,最後四個人的婚姻都應(yīng)了和尚的話,一個個落得離婚的結(jié)局。這篇寫的是現(xiàn)代人的離婚群像。四個女人經(jīng)歷結(jié)婚、出軌、離婚、移民,被敘述者“我”輕描淡寫,又透著疼痛。周潔茹把女性在婚姻中的離散、聚合、精神疼痛全寫出來了,那麼深刻而又到位。
再看另外一組小説:《幸福》和《生病》。《幸福》的講述者還是第一人稱的“我“,小説主角是小“我”四歲的侄女毛毛,主要情節(jié)是毛毛與兩個男人(青梅竹馬的富二代魏斌和鄉(xiāng)下青年景鵬)的戀愛故事。魏斌對毛毛百般呵護,毛毛卻不愛他,她夾在兩個男人之間,後來毛毛意外懷了孩子,打胎過程得了腹腔炎,醫(yī)院診斷她今後有生育困難。故事發(fā)生的場景大多集中在醫(yī)院,這點與《生病》有著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幸福》以反諷手法,聚焦女性的身體、權(quán)力、價值依附的問題。女主角毛毛是一個沒有自理能力又對金錢沒有概念的女人,她是《尖東以東》裏拜物教信徒的翻版,毛毛租的房子堆滿名牌包包和奢侈品,她的身體成了生育和維繫幸福的工具。《幸福》中的毛毛被剝奪了話語權(quán),她既沒有很好的學(xué)歷又缺乏謀生能力,與景鵬也沒有共同語言。小説借“我”之口道出毛毛戀愛的悲劇,毛毛和景鵬唯一的共同語言在床上;而《生病》的女主角珍珠像極了另一版本的毛毛。“珍珠説,我的血永遠凝固不起來的,所以我不能生小孩的。”珍珠遭德籍華裔男友的嫌棄,戀愛告吹,因為生病住進醫(yī)院,敘述者“我”去醫(yī)院陪護,由此展開敘述。《生病》由片段組成,沒有具體的情節(jié),寫法上與《結(jié)婚》異曲同工。
從敘事方式上來看,四篇小説都採用第一人稱,講的是“閨蜜”之間的故事。敘述者“我”承擔(dān)了講述故事的功能:“我”既在內(nèi),又在外,既疏離,又融合。從小説整體的批判維度和審美內(nèi)涵來説,它們是女性經(jīng)驗的集體呈現(xiàn),從頭到尾,女性的傷痛、離散、創(chuàng)傷記憶等經(jīng)驗是“在場”的,但吊詭之處在於,這些女性在現(xiàn)代社會的話語場域中始終居於邊緣,她們看似發(fā)聲實則沉默。或許與作者在刻畫男性形象上的模糊處理有關(guān)。他們的身份,有的是富二代、有的是到大城市奮鬥的鄉(xiāng)下青年,有的是醫(yī)生,有的是教授,無論地位身份還是價值體系,都與周潔茹筆下這些受傷的女子迥異。男性形象的模糊描寫也是某種“缺席”,他們與女性經(jīng)驗的“在場”構(gòu)成互補。在女性“失聲”的地方,父權(quán)制社會的男權(quán)話語體系反而淩駕其上。
三. 異與同:小説敘事的雙重奏
在香港故事中,周潔茹將故事的發(fā)生場所安排在香港的不同地理空間,並且苦心孤詣地以香港地名作為小説題目,這批小説處理的經(jīng)驗驚人的相似:女性個體的生存空間與香港這座“孤島”間微妙複雜的關(guān)係。在這點上,周潔茹的“香港股市”存在鮮明的“同構(gòu)性”,用許子?xùn)|的話來説,它們呈現(xiàn)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香港小説”一以貫之的“失城意識”,許子?xùn)|稱之為“此地他鄉(xiāng)”,即身在此,意在彼,小説人物的歸屬感始終是游離的;而在另一條創(chuàng)作軌跡上,周潔茹勾勒出婚姻愛情中處於“愛與痛的邊緣”的系列女性形象,她書寫女性的經(jīng)驗和傷痛記憶。這批小説的空間地理通常是模糊的,只作為背景呈現(xiàn)。讀者讀到的都是現(xiàn)代都市的“速寫”印象:咖啡館、電影院(《離婚》)、醫(yī)院(《幸福》)……此外較耐人尋味的是小説的“異國”形象,《離婚》中的女人,總是(想)嫁去異國他鄉(xiāng):加拿大、美國……異國他鄉(xiāng)在這裡只是作為表層的空間地理符號而存在,就其深層結(jié)構(gòu)來看,它們也構(gòu)成了女性“逃離”傷痛記憶,試圖開始新生活的精神空間(或許可以理解為這與周潔茹曾經(jīng)的海外生活相關(guān),它們共同構(gòu)成周潔茹小説另一個尚待開拓的領(lǐng)域)。這點容易令人聯(lián)想到愛麗絲·門羅那些書寫女性“逃離”的小説。然而周潔茹始終站在“此岸”冷靜克制地觀望“彼岸”。小説《離婚》中的女人並沒有因為去到國外嫁給外國人而獲得幸福。周潔茹筆下的“她們”一直處在分裂焦慮的精神狀態(tài)下。
行筆至此,可以看到周潔茹的兩條創(chuàng)作軌跡在涉及到女性生存經(jīng)驗、價值認同、道德倫理等維度上重疊並交匯。香港故事充滿女性經(jīng)驗,女性故事包含香港經(jīng)驗,二者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在此基礎(chǔ)上勘察周潔茹小説的敘事風(fēng)格和審美旨趣或許更有意義。
周潔茹擅長在行文中用簡練的甚至跳躍的語調(diào)講故事,她不動用大篇幅的筆墨來細描,涉及到小説中“場景”的部分,都是一筆帶過,從來不花費巨大篇幅進行繁複細緻的描繪。那麼,是什麼構(gòu)成了她小説敘述的主體部分?筆者認為有以下幾方面:(1)利用人物對話推進情節(jié)。這或許是當(dāng)代小説尤其是短篇小説敘事的一大特色,試看美國作家海明威和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説,前者有“冰山理論”,後者被冠以“極簡主義”的美譽,二者的共同點都是簡練流暢的人物對白,某種程度上接近劇本的形式。周潔茹的“香港故事”也好,女性系列也罷,人物的對話顯得流暢、細膩,遊刃有餘,這批小説寫出了獨屬於“閨蜜”的語言風(fēng)格;(2)人物心理的帶入帶出,就像電影畫面的淡入淡出,周潔茹將人物心理情緒的涌動通過間接引語直接附著于文本中,讀者有時分不清這些言論究竟是虛構(gòu)人物的,還是作者自己的。考慮到作者的女性地位,如此疑慮又顯多餘了。我們可以假定,周潔茹筆下女性的心聲便是作者的心聲,她們的傷痛與憤怒、孤獨與絕望,是現(xiàn)代社女性心理情感的同位語;(3)第一人稱敘事的頻繁使用。周潔茹小説的譜係中隨處可見作者的“自傳性”乃至敘事聲音的介入,可以説“我”的影子在文本中無處不在。即便在貫穿第三人稱敘事的《到香港去》和《旺角》,第一人稱敘事也成了潛在的結(jié)構(gòu)。這點與周潔茹的香港/美國生活經(jīng)歷息息相關(guān),甚至可以認為它們只是作者生活的切片,它們被放置在小説這一顯微鏡下,成了標(biāo)本。透過小説的放大作用,能清晰地看見其紋路、肌尖理和組織構(gòu)造——它的病灶、癌變乃至死亡徵兆,其實都無比清晰地映照出當(dāng)代社會中女性個體生存的隱憂。
這是周潔茹小説敘事的雙重奏:香港故事與女性經(jīng)驗水乳交融,彼此依存。我們有理由相信,周潔茹接下來還會繼續(xù)寫她的“中國故事”和“美國故事”,這三者會構(gòu)成她寫作疆域重要的版圖。周潔茹的短篇小説大體採納現(xiàn)實主義的寫作手法,沒有實驗和後現(xiàn)代主義,她的小説也不需要取巧于形式的先鋒。周潔茹的小説介於通俗與嚴肅之間,在觀照世相與描繪情事之間遊刃有餘。換言之,我們無需為周潔茹貼上任何標(biāo)簽,她筆下的人物活得如此立體,當(dāng)代社會的隱約變遷,新媒體(QQ、微信等)的使用,在她的虛構(gòu)世界中並置著,絲毫不顯突兀。許多當(dāng)代小説家寫作上的缺陷在於,他們總是刻意在文本中彰顯自身的創(chuàng)作意圖,努力貼近時代,野心太大,格局太小;相反,周潔茹看似無意去經(jīng)營宏大敘事,也無意于表徵時代,但往往無心插柳,將時代和社會的幽微處揭露出來,如是,雙聲部匯聚成單聲部,雙重奏也是多重奏。
[責(zé)任編輯:楊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