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莎士比亞作品究竟是否出自莎翁之筆一直眾説紛紜。近日,林菲爾德大學的丹尼爾·波拉克·佩爾澤教授在《紐約客》撰文,題為“新版牛津《莎士比亞全集》的激進觀點(The radical argument of The New Oxford Shakespeare)”,介紹了莎翁考證的最新進展。
去年,蓋瑞·泰勒擔任主編的新版牛津《莎士比亞全集》出版,這套全集還破天荒地將多位劇作家確認為15部莎士比亞戲劇的合著者,其中包括確認了著名劇作家馬洛為《亨利六世》的合著者。在《紐約客》的文中,佩爾澤援引泰勒的話指出,神化莎士比亞造成了世人對其他文藝復興時期才華相當?shù)膭∽骷业拿ひ暎疑勘葋喌臍v史觀、講故事的方式被確認為典範,而其他的歷史想像、講故事的方式則被忽略。下文為《紐約客》刊登的文章之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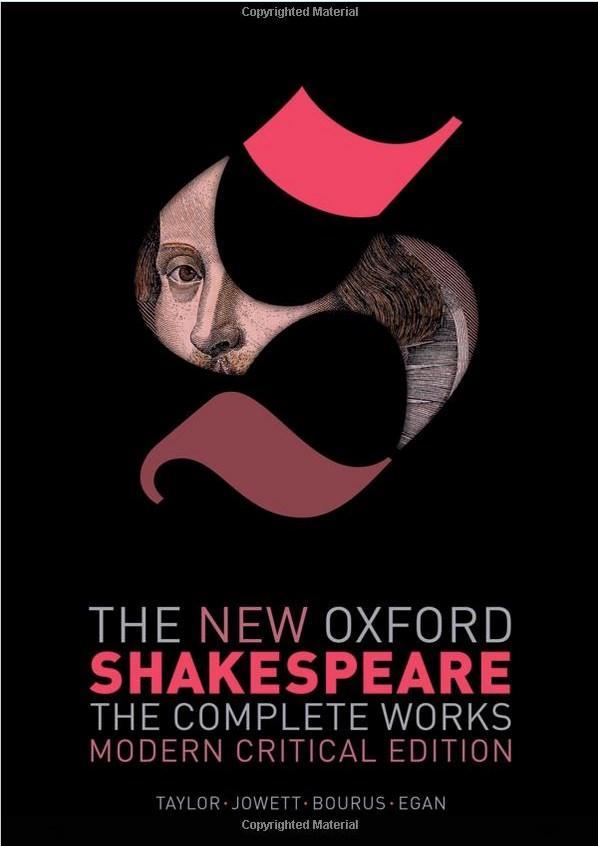
蓋瑞·泰勒擔任主編的新版牛津《莎士比亞全集》
1989年,一位叫蓋瑞·泰勒的年輕學者出了一本書叫《重新發(fā)明莎士比亞》,書中認為莎士比亞至高無上的文學地位更多來自那些將他推上神壇的文化制度,而不是他作品本身的偉大。歸功於這些文化制度,莎士比亞傲視于文藝復興時期與他有著同等才華的劇作家。“莎士比亞是一顆璀璨的明星,但他從來不是我們的星系裏唯一一顆。”泰勒寫道。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拋出這類挑戰(zhàn)正統(tǒng)的言論。幾年前,他就擔任過牛津版《莎士比亞全集》的主編之一,這套全集認為莎士比亞的五部戲劇是與人合著的。
去年底,泰勒再一次震驚世人,由他擔任第一主編的新版牛津《莎士比亞全集》出版。這套全集第一次把克裏斯托弗·馬洛認定為《亨利六世》的合著者,主要創(chuàng)作了前三部分。此外,這套全集還列出了其餘14部莎士比亞戲劇的合著者——托馬斯·納什、喬治·皮爾、托馬斯·海伍德、本·約翰遜、喬治·威爾金斯、托馬斯·米德爾頓和約翰·弗萊徹。泰勒是如何發(fā)現(xiàn)這些劇作是合著而非莎氏獨撰的證據的?答案是通過大數(shù)據來分析早期劇作的語言模式。為此泰勒在一次發(fā)佈會上打趣説:“現(xiàn)在莎士比亞也進入了大數(shù)據時代”。
當然,認為莎士比亞的劇作非他獨創(chuàng)産物的觀點也早已不新鮮,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在16世紀進行戲劇創(chuàng)作有點像今天的劇本創(chuàng)作,往往經多人之手修改後方能付梓。新版牛津莎翁全集認為它的演算法可以辨別出哪些作品是以一人之力完成的。但這部新版全集的意義還不在於指出哪些莎翁作品是合力為之,也不在於重新發(fā)現(xiàn)並承認與莎翁同等重要卻被忽視的劇作家,而是指出,對於莎士比亞的神化決定了他講故事的方式——尤其是他那種君主中心的歷史觀——對於我們來説已經成為了毋庸置疑的規(guī)範,而實際上存在著其他講故事的方式,其他的歷史觀,在這些方面,別的劇作家要比莎士比亞更優(yōu)秀。

馬洛畫像
長期以來,學者一直把馬洛和莎士比亞看成一對惺惺相惜的競爭對手。莎士比亞的《理查三世》可能模倣了馬洛的《帖木兒》和《浮士德》,《威尼斯商人》可能借鑒了馬洛的《馬爾他的猶太人》,而馬洛在創(chuàng)作自己的悲劇《愛德華二世》時參考了莎士比亞的歷史劇。但新版牛津全集所認為的馬洛和莎士比亞共同創(chuàng)作了《亨利六世》的觀點卻並未受到主流認同,而且其數(shù)據分析的方法論也廣受質疑。
一個世紀以來,學者們一直都在試圖對莎士比亞的風格進行量化分析。1901年,一位氣象學家就雇了兩位女性計算莎士比亞及其他著名作家作品中每個詞的字母數(shù)量。當代的考證學方法則更複雜,但也只是程度有別,而非質的差別。泰勒也曾根據功能詞之類的語言學特徵來考證,比如像by、so、from這些詞很可能是下意識的,很難故意模倣。
對於考證出馬洛是《亨利六世》的合著者,泰勒提到最新一期《莎士比亞季刊》的文章。這篇文章檢查了一個劇作家如何可能在某個功能詞後用另一個功能詞。譬如,《哈姆雷特》裏那句“With mirth in funeral and with dirge in marriage”裏,決定性的詞是“and with”,這個功能詞的組合在莎士比亞的作品中更常見。而馬洛式的表達在《亨利六世》中出現(xiàn)多次。該文作文承認他們的方法並不完美,而且可能張冠李戴。
有人指責泰勒説他對莎士比亞懷有恨意,但事實上他是莎士比亞的崇拜者。但他認為我們對於莎士比亞的才華的神化造成了我們對於其他卓越劇作家的盲視,以及他們所提出的另類政治想像。
“莎士比亞最喜歡的主題是君主制、專偶制、一神制,與此相應的,他最富盛名的臺詞和十四行詩都是獨白。”莎士比亞對唯一性、獨一性情有獨鍾,而泰勒則相信讀者的民主,他們喜歡什麼東西無需他人置喙。
長期以來,學者們都會借莎士比亞的獨一無二來貶低其他劇作家。當批評者發(fā)現(xiàn)莎氏早期和晚期作品中某個糟糕的段落或有違和感的地方時,一個解決辦法就是將之怪罪于一個劣等的合著者。莎翁之神聖不可侵犯還體現(xiàn)在,有人會認為其他人的華彩段落其實出自莎翁之手。譬如,佚名之作《托馬斯·莫爾爵士》就被認為是莎翁之作,因為筆跡與莎翁現(xiàn)存的六種簽名相符。儘管這個理由有點牽強,但想發(fā)現(xiàn)新的莎翁手稿的渴望卻非常具有誘惑力,他們還硬生生地把莎士比亞和莫爾駁斥反移民暴徒的滲透自由主義色彩的段落聯(lián)繫在一起。是不是只要是莎士比亞,就是好的?或者説只要是好作品,我們就覺得那是莎士比亞的作品?
出於這種假設,許多編輯往往就會認為《亨利六世》中某些段落出自托馬斯·納什或喬治·皮埃爾之手,這些段落被認為是粗鄙錯漏的。馬洛全集的編者之一拉斯馬森對泰勒把作者考證和藝術價值的判斷分開的做法表示讚賞,“如果他吹捧《我該死嗎》,每個人都會説,這個戲很垃圾。但如果是莎士比亞,那大家就會説莎士比亞應該是好的,而這部有美學缺陷。大錯特錯!你隨便找一部劇,你都可以發(fā)現(xiàn)那些我們認為是莎士比亞的美學上糟糕的地方。”

莎士比亞畫像
對於泰勒來説,如果我們把莎士比亞看成許多明星中的一顆而非唯一,那將讓我們看到其他類型的文學價值,而不是認為如果與莎士比亞不同,那文藝復興時期的其他劇作家就不好。十年來,泰勒堅持認為米德爾頓是“我們另一位莎士比亞”。而就最近報章連篇累牘的報道來看,馬洛則有望成為一顆更性感的明星。而且更重要的是,馬洛對於《亨利六世》的貢獻可能表明存在另一種講述歷史的方式。
在新版牛津《莎士比亞全集》裏,《亨利六世》第二部的一個最初的標題是《約克和蘭開斯特家族之爭的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之所以變成《亨利六世》第二部是因為莎士比亞幾年前改寫了前傳。莎士比亞決定把他的歷史劇當成國家建設的一部分,要把君主放在標題裏,後來的劇作也是這麼印刷的。“如果你把《亨利六世》第二部看成與人合著的,你會看到一種不同的歷史劇是如何可能的。”泰勒説。
泰勒的團隊將這種不同的歷史劇的可能性歸功於馬洛,相較于莎士比亞側重男性君主,馬洛更側重於強悍的女性角色如聖女貞德和反叛的平民。
“莎士比亞並沒有發(fā)明歷史劇,他是重新發(fā)明瞭歷史劇,使它更強調君主、偉人。如果你意識到《亨利六世》尤其是第二部裏有兩種政治想像的話,那就非常有意思了。”泰勒説。
泰勒認為這兩種互相對立的政治想像具有超出文本外的意義。“劇中不止發(fā)生著一場政治內戰(zhàn),而且發(fā)生著一場美學內戰(zhàn)。《爭論的第一部分》(The First Part of the Contention)是第一部偉大的英國歷史劇。馬洛和莎士比亞都是冉冉升起的新星,二人都是匠人兒子,都不是在大都市長大的,也都雄心勃勃。這兩位非常優(yōu)秀但迥異的劇作家都在想像新的戲劇形式是什麼樣的,”泰勒補充道,“可以説莎士比亞贏了,因為馬洛被刺殺了。在職業(yè)生涯之初,你絕對無法明確判斷説莎士比亞更偉大。如果馬洛再多活二十年,我們可以想像他會提供非常不同的講述歷史、悲劇和喜劇的模式。”( 文/丹尼爾·波拉克·佩爾澤,編譯/沈河西)
[責任編輯:楊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