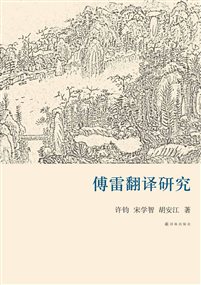
時光荏苒,傅雷先生已經離開我們五十年了。五十年的時間可以改變很多事情,但未能改變的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在今天依然具有獨一無二的價值。他所寫就的家書和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仍為讀者所喜愛,就證明了這一點。
在其翻譯生涯中,傅雷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譯作,如《名人傳》《約翰·克利斯朵夫》等,至今它們仍然是眾多讀者的首選譯本。以這些譯作與其翻譯觀為主體,傅雷構建起一個宏大的翻譯世界。這個世界也成為研究者持續(xù)探索的對象,角度各有不同的相關著作屢見,而許鈞、宋學智和胡安江近著《傅雷翻譯研究》無疑把對這個世界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傅雷在弱冠之年遠渡重洋,前往法國留學。在法期間,傅雷以藝術為其學業(yè)方向,意圖用西方的藝術來改變國人的精神,從而促成整個國家的新生。然而歸國之後,由於性格剛直,面對社會的“陰霾”不肯妥協(xié),他最終選擇閉門譯書,由此開始了貫穿其一生的翻譯事業(yè)。在之後的三十餘年中,雖經世事變化,傅雷始終有自己秉持的原則,那就是翻譯要與時代相合,發(fā)揮推動社會前進之作用。
1934年,傅雷致信羅曼·羅蘭,談及自己翻譯其《名人傳》的想法。在當時中國動蕩的背景下,他認為民眾“顧精神平穩(wěn)由之失卻,非溺于激情而懵懵懂懂,即陷於麻痹而無所作為”,亟待拯救,而貝多芬“莊嚴之面目,不可搖撼之意志,無窮無竭之勇氣”,彌蓋朗琪羅“意志與才力不稱”之悲劇,托爾斯泰之“不抵抗主義”,均可引發(fā)民眾之深思與自省,獲取“莫大啟示”。稍後,1936年至1941年,傅雷又翻譯了《約翰·克利斯朵夫》。其間,中國的形勢絲毫不見好轉,反而因日本的侵略而陷入更大的困境。面對如此國情,傅雷選譯此書,併為之付出大量心血。在該書“譯者獻辭”中,他説:“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而在第二卷的“譯者弁言”中,他對主人公克利斯朵夫作了深入剖析,認為這一人物擁有質樸的精神和英雄的意志,其成長經歷了自強不息、不斷奮鬥的過程,他“應當是人類以更大的苦難、更深的磨煉去追求的典型”。這樣一個人物形象,對於身處苦難之中的國人而言是莫大的激勵,也是值得效倣的對象。同樣,在翻譯其他作品,包括解放之後翻譯巴爾扎克作品和政論性文章時,傅雷的目光都並非僅投放在單純的文本之上,而是看到時代的需要。可以説,“傅雷的翻譯選擇,始終與其懷抱的一顆憂國憂民之心緊密相連”。
在半個多世紀之後的今天,傅雷的立場仍然是我們要堅持的。當下,為滿足新時代中新的讀者需求和社會發(fā)展需要,翻譯很繁榮,佳作也頗多。但不容忽視的是,其中也混雜了一些恐怕不那麼有價值的作品。究其原因,在於引進時過於考慮迎合部分讀者的需求,而忽視了更為重要的推動社會進步的責任。
傅雷的譯作跨越八十年的時間,今天仍受熱捧,傅雷作為譯者賦予作品能經受時間考驗的新語言形式,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種新語言形式裏面體現(xiàn)了傅雷那博大精深的翻譯觀。
1951年,在《〈高老頭〉重譯本序》開篇,傅雷寫道:“以效果而論,翻譯應當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之所以提出這一“神似論”,是因為他對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實在是認識到了骨子裏:兩國文字在各個方面有著太大的距離,翻譯“只能儘量縮短這個距離”,而無法使其消失。傅雷是這樣想,也是這樣做的。《傅雷翻譯研究》裏對《都爾的本堂神甫》中對話的翻譯的研究,明確無誤説明瞭這一點。作者找出了傅雷翻譯《都爾的本堂神甫》的初稿、二稿和定稿,通過比較發(fā)現(xiàn),在有些對話上,傅雷前後做出了不少改動,從而使對話更貼合説話者的性格及對話發(fā)生的語境,同時更像真實的中文日常話語。這裡面,傅雷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原文文字層面的限制,而抓住了背後的神韻,也使譯文更為中文讀者所接受。這一“神似論”與中國傳統(tǒng)藝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繫,體現(xiàn)了傅雷身為一位翻譯家所具有的廣博藝術素養(yǎng)。
傅雷在《翻譯經驗點滴》中談到,從文學的類別和派別兩個方面而言,譯者都應該認清自己的界限,這個界限包括了能力、適應力、熱愛程度等多種因素。只有具備了這種自我認識,才能發(fā)揮自己所長,將一部作品恰如其分地翻譯過來;否則,不會作詩的人強要譯詩,“弄得不僅詩意全無,連散文都不像”,這樣的局面,想必詩人、譯者和讀者都不願看到。
三十多年中,傅雷翻譯了數(shù)十部外國文學作品。在這數(shù)以百萬計的文字裏面,要以一個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句子作為代表,那一句“江聲浩蕩”無疑會迴響在很多人的耳邊。“江聲浩蕩,自屋後上升。”傅雷以這九個字來翻譯《約翰·克利斯朵夫》這部“長河小説”的第一句話,引出後面百萬餘言,可以説恰到好處。正如有人所言,“這四個字有一種氣勢,有一種排山倒海的力量,正好和書中的氣勢相吻合”。原文同樣的一句話,在他人的譯本中有不同的表達,其所形成的效果或許可以説各有特色,但若以簡潔有力、與原作精神相契合而言,則傅雷的這九個字更勝一籌。而如果我們將視野擴大,俯視整部作品,仔細體察,便會發(fā)現(xiàn),羅曼·羅蘭的這個句子並非獨立的,而是在全書的尾聲,以同樣的句子作為回應,讓兩處“江聲”相激蕩,造成更為宏大的氣勢。這樣一種跨越百萬言的前後呼應,被有的譯者忽視了,卻沒有逃過傅雷的眼睛。他以與開頭同樣的譯文,再現(xiàn)了作者的意圖。見微知著,傅雷“是基於其自身對原作的整體理解與把握,基於對原作者意圖和本文意圖的辯證關係與內在聯(lián)繫的領悟,達成了譯者與原作者視野與思想的溝通和融合”。這是一種站在作品整體高度、通觀全局的翻譯視野。
如前文所言,造就傅雷翻譯事業(yè)高度的有他的家國情懷、赤子真情、藝術素養(yǎng)、自我認識,以及不懈追求文字極致境界的精神;這一個個高度相疊,共同形成了今天讓我們仰止的高山。我們應該感到慶倖,有這樣的高山在前,讓我們得以攀登其上,欣賞更為遼闊的風景;也啟迪後人,讓我們塑造更好的翻譯世界。
[責任編輯:楊真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