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dāng)我們已經(jīng)習(xí)慣有問題找警察,有糾紛找法官時,在“皇權(quán)止于縣政”的時代,鄉(xiāng)村的社會秩序、倫理道德如何維繫?“鄉(xiāng)紳”成為一個繞不過去的重要群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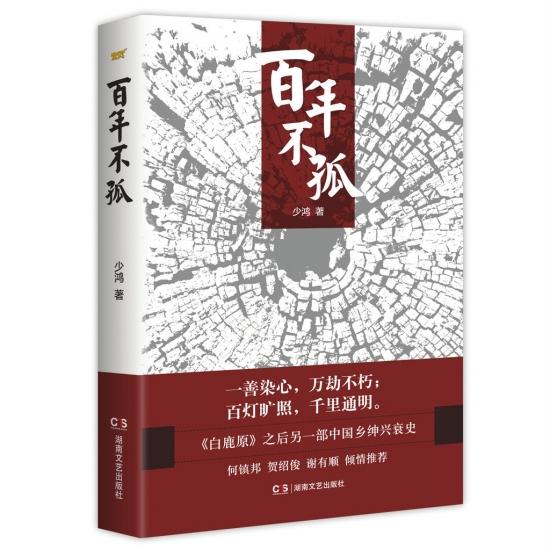

陶少鴻
湖南省作協(xié)名譽(yù)主席陶少鴻,進(jìn)城已有幾十年,然而他的筆下寫得更多的卻是鄉(xiāng)村。雖然當(dāng)過工人、進(jìn)過大學(xué)、做過機(jī)關(guān)幹部,但他説,“無論身份如何變化,還是覺得自己是個鄉(xiāng)下人,因為故鄉(xiāng)永遠(yuǎn)是你的精神胎盤”。
如果説他七年前寫的《大地芬芳》是關(guān)於中國農(nóng)民的生存問題,那麼新作《百年不孤》探討的就是關(guān)於人的“精神歸宿”。這是一部關(guān)於中國鄉(xiāng)紳命運(yùn)的長篇小説,跨度百年,在他看來,“鄉(xiāng)紳作為一個特殊群體,曾經(jīng)是鄉(xiāng)村倫理的維護(hù)者,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者。”
然而,在當(dāng)代中國文學(xué)長廊裏,鄉(xiāng)紳的身影被遮蔽。陶少鴻想直面歷史與人性,塑造一個全面、完整、真實(shí)的鄉(xiāng)紳形象。
鄉(xiāng)紳不是官,卻是基層治理的主角
“土豪劣紳”,這是今天人們“熟悉”的“鄉(xiāng)紳”。
他們究竟是一群什麼樣的人?
“鄉(xiāng)紳”者,乃“在鄉(xiāng)縉紳”之謂。“縉紳”字典裏的解釋指的是古代有官職或者做過官的人。由此可知,鄉(xiāng)紳與“官”有著密切聯(lián)繫。
明清時期的鄉(xiāng)紳由這樣一群人組成:致仕、卸任甚至被罷免的回鄉(xiāng)官員,以及現(xiàn)任官員在家鄉(xiāng)的親戚子弟;府州縣學(xué)的生員、國子監(jiān)的監(jiān)生,以及在鄉(xiāng)試、會試中及第的舉人和進(jìn)士。
“這兩類人雖然與現(xiàn)任官員不同,但前者是曾經(jīng)做過官的人,後者則是將要做官的人(進(jìn)士大多例外)。”山東師範(fàn)大學(xué)教授徐繼存説。
他們不是官,卻是基層治理的主角。他們處在國家與鄉(xiāng)村社會之間,扮演著獨(dú)特的政治角色與社會角色。
《百年不孤》塑造的岑勵畬、岑國仁父子是典型的鄉(xiāng)紳,前者是晚清秀才,寫得一手好字,講究禮性,樂善好施。後者岑國仁曾給縣長當(dāng)秘書,見不慣殺人逃了回來,算得上是回鄉(xiāng)的“官”。
在《百年不孤》描寫的雙龍鎮(zhèn)有這樣的習(xí)俗,無論是分家、不動産買賣還是鄰里糾紛,都得有中人來做評判與見證,也得由中人來調(diào)解。
中人往往由德高望重的人擔(dān)當(dāng),才讓人信服。而在雙龍鎮(zhèn),最權(quán)威的中人非岑勵畬莫屬。李家兩個兒子分家,房子一大一小,兩個兒子相爭不讓,就請岑勵畬做中人調(diào)解了斷。
陶少鴻筆觸細(xì)膩,許多細(xì)節(jié)故事如同真實(shí)發(fā)生過。“實(shí)際上,岑勵畬、岑國仁父子是有原型的,是從我外公的家族故事生發(fā)而來,某些事件也的確真實(shí)發(fā)生過。”他説。
在“皇權(quán)止于縣政”的時代,“村子裏沒有行政機(jī)構(gòu),沒有法官、法庭,就靠鄉(xiāng)紳來維護(hù)鄉(xiāng)村的秩序。”陶少鴻説。
撰寫《鄉(xiāng)土中國》的費(fèi)孝通對此有專門論述:“在政府的傳統(tǒng)體系內(nèi),中央權(quán)力的觸覺停滯在縣裏。每個縣通常是由村民在地方上組織起來的一系列村莊所組成的。地方組織有著共同的財産,管理共同的事務(wù),如宗教儀式和澆灌。這種組織的當(dāng)事人不是由所有家庭裏的代表選舉出來的,而是由村莊裏受尊敬的長者決定的。受尊敬的長者是那些有土地和身份的人,即那些和官方以及鎮(zhèn)上紳士有聯(lián)繫的人。”
大多數(shù)鄉(xiāng)紳顧及一方聲望和名譽(yù)
鄉(xiāng)紳裏有沒有“劣紳”?當(dāng)然有。
但徐繼存認(rèn)為,“儘管鄉(xiāng)紳賢愚優(yōu)劣,固有不齊,但由於鄉(xiāng)紳深受儒家文化浸潤,他們大都認(rèn)為自己理所當(dāng)然地負(fù)有造福家鄉(xiāng)的使命,具有完善、維持地方和宗族組織的責(zé)任。”
《百年不孤》中,為了減少溺女嬰的惡習(xí),主人公岑國仁索性成立了育嬰會,“凡家庭貧困的人家,生女孩就資助一旦谷養(yǎng)育糧”。遇到災(zāi)荒年份,岑家開義倉救濟(jì)。遇到河流攔路,岑家祖輩帶頭捐資修建風(fēng)雨橋。
“其實(shí),這些事都真實(shí)發(fā)生過。”陶少鴻説。“至今,湖南安化有一座永錫橋,是安化有名的旅遊景點(diǎn),就是我外公的祖父聯(lián)合一些鄉(xiāng)紳修建的,橋頭至今還立著功德碑,寫著他們的名字。”
“鄉(xiāng)紳們做善事的原動力來自於哪?”我問他。
陶少鴻認(rèn)為與文化傳承和文化環(huán)境有關(guān)。“做善事,對於他們來説,是一種好的名望,會引來村民的尊崇。”
“面子”是《百年不孤》中隱約提到的另一個原因,主人公鄉(xiāng)紳岑國仁開倉放糧,重建義倉,村裏人嚼舌頭,“他是想要個吾之公那樣的好名聲吧。”
費(fèi)正清説。“‘面子’是個社會性問題。個人的尊嚴(yán)來自行為端正,以及他所獲得的社會讚許。”
因此,鄉(xiāng)紳大都很注重自己的身份和行為,顧及自己的聲望和名譽(yù),講究“面子”。
“如果鄉(xiāng)紳在行為上有失檢點(diǎn),嚴(yán)重違反這些道理,那麼他在農(nóng)民中的威望也就喪失了,鄉(xiāng)紳中的絕大多數(shù)都不樂意讓自己的桑梓地的農(nóng)民看不起。”中國人民大學(xué)教授張鳴説。
而鄉(xiāng)紳的行為,反過來又可成為鄉(xiāng)民的表率和法則。正如江西巡撫沈葆楨所寫的《居官圭臬》所雲(yún)“大凡一方有一個鄉(xiāng)紳,便為那一方的表範(fàn)。鄉(xiāng)紳家好刻薄,那一方都學(xué)得刻薄;鄉(xiāng)紳家好勢利,那一方都學(xué)得勢利了。若還有一個鄉(xiāng)紳儉樸淳篤、謙虛好禮、尊賢下士、凡事讓人,那一方中,哪個不敬重他、仰慕他。”
“一個農(nóng)民從生到死,都得與紳士發(fā)生關(guān)係”
“一個農(nóng)民從生到死,都得與紳士發(fā)生關(guān)係。”費(fèi)孝通説。
在滿月酒、結(jié)婚酒以及喪事酒中,都得有紳士在場,“他們指揮著儀式的進(jìn)行,如此才不致發(fā)生失禮和錯亂。在吃飯的時候,他們坐在首席,接受主人家的特殊款待”。
對於大字不識的農(nóng)民而言,文字是具有神秘性和權(quán)威性的。
《百年不孤》中,岑國仁捧著寫廢的字紙,走到路旁的一座六邊形四層的寶塔旁,將字紙倒入其中,劃一根洋火點(diǎn)燃。這座塔就是字紙塔,塔身上刻著“敬惜字紙”的字樣。“這也並非杜撰,湖南許多地方都有這樣的塔。”陶少鴻説。
讀到這個細(xì)節(jié),在《百年不孤》的新書發(fā)佈會上,評論家賀紹俊説,“原來,以前的人對文化如此尊崇。”
因此,陶少鴻對“鄉(xiāng)紳”有一個定位,“鄉(xiāng)村倫理的維護(hù)者,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者。”
然而,當(dāng)“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來臨,鄉(xiāng)紳開始陸續(xù)分化和衰微,有的棄鄉(xiāng)入城,有的投資辦廠,有的轉(zhuǎn)向自由職業(yè)……
當(dāng)上個世紀(jì)60年代,十幾歲的陶少鴻被下放到安化農(nóng)村時,他還能看到這樣的景象。夜晚,若有手藝人經(jīng)過,請求留宿,“村民們會無條件接待,不要報酬,還特意打兩個荷包蛋。”村裏會設(shè)置涼亭,涼亭裏常駐一人,每天燒一大桶水,供來往的人飲用。過河會有義渡,免費(fèi)將人渡過河。“這些都是一種制度性安排,由當(dāng)?shù)厝颂峁┮粌蓳?dān)谷的報酬給涼亭燒水的村民。”
“扶助鄉(xiāng)民,這是‘賢者’應(yīng)盡的責(zé)任”
當(dāng)陶少鴻寫出《百年不孤》時,《“十三五”規(guī)劃綱要(草案)》恰巧提出了“新鄉(xiāng)賢文化”。
“鄉(xiāng)紳和鄉(xiāng)賢有什麼樣的共同點(diǎn)和區(qū)別?”
“鄉(xiāng)紳已然消失,鄉(xiāng)賢也不是鄉(xiāng)紳,他們的共同點(diǎn)是都是鄉(xiāng)村的優(yōu)秀人物,都是鄉(xiāng)村精神領(lǐng)袖,”陶少鴻説,“不同點(diǎn)在於鄉(xiāng)賢沒有歷史附著在鄉(xiāng)紳身上的封建的消極因素,反而能更好地繼承和發(fā)揚(yáng)傳承下來的優(yōu)秀文化與道德精神,起到營造現(xiàn)代鄉(xiāng)村文化與道德倫理的作用。”
1999年,韓少功回到曾經(jīng)插隊的汨羅建了一座小院子“梓園”。他掏5000元給村裏修水渠。為了鄉(xiāng)里的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向當(dāng)?shù)厥形瘯泴懶拧坝憽边^錢;村子裏為修路規(guī)劃吵吵鬧鬧,村長請“韓爹”來説了幾句話。如今,“韓爹”是八景最有“話份”的人。
2016年3月24日《人民日報》登載一篇評論《“新鄉(xiāng)賢”新在哪兒》比較了新鄉(xiāng)賢與鄉(xiāng)紳的區(qū)別後提出,“無論怎樣‘新’、怎麼‘變’,‘鄉(xiāng)賢’的責(zé)任義務(wù)沒有變。”
“一個人‘賢’與否,關(guān)鍵看他對‘不中’‘不才’之人,是‘養(yǎng)’還是‘棄’;照顧貧弱、扶助鄉(xiāng)民,這是‘賢者’應(yīng)盡的責(zé)任。”
從寫小説的角度來説,寫“好”比寫“壞”更難。寫“壞”寫出一個壞處就可以,而寫“好”必須“好”得邏輯清楚,沒有破綻。
《百年不孤》中,岑勵畬、岑國仁父子是“極善”,開倉放糧救濟(jì)難民、設(shè)立育嬰堂防止溺女嬰,“當(dāng)然,他們也會有搖擺和內(nèi)心糾結(jié)的時刻,重要的是,他們最終選擇了善舉。”
陶少鴻説,“直面歷史與人性,塑造一個全面、完整、真實(shí)的鄉(xiāng)紳形象,為他們傳承下來的傳統(tǒng)美德點(diǎn)讚,是我寫這部小説的緣起與初衷。”
對話
故鄉(xiāng)永遠(yuǎn)是你的精神胎盤
瀟湘晨報:您説小説契機(jī)是自己寫作的原動力與內(nèi)驅(qū)力,只有它出現(xiàn)了,才會寫小説,才能寫小説,《百年不孤》這部小説的契機(jī)和觸發(fā)點(diǎn)是什麼?
陶少鴻:這部小説的主人公岑勵畬、岑國仁父子的原型就是我外公。岑國仁的兒子岑佩琪與我舅舅的經(jīng)歷一模一樣,甚至後來在小説中揭發(fā)自己二叔的事也是真實(shí)的。我寫這部小説,就想寫出幾代人作為一個鄉(xiāng)紳,創(chuàng)業(yè)奮鬥、樂善好施的故事,是鄉(xiāng)村文化領(lǐng)袖的最後見證,是一部集家族、創(chuàng)業(yè)、精神傳承于一體的百年史。
瀟湘晨報:因為主人公的原型是自己的家人,寫作的時候,有沒有可能美化?
陶少鴻:我自己覺得沒有,我寫他們的時候,不會有意拔高,如果拔高,塑造這個人物就失敗了。原型就是提供我一個契機(jī),給了我一個感悟。
瀟湘晨報:您曾説《大地芬芳》這部小説是您最看重的小説。那麼,現(xiàn)在《百年不孤》出版了,它在您心中是怎樣的位置?
陶少鴻:《大地芬芳》是寫我父輩的故事,也有一些原型。《百年不孤》寫的是母系長輩的故事。前者講述農(nóng)民如何獲得土地,關(guān)於人的生存;後一部小説是關(guān)於人的精神歸宿。這兩部可以互補(bǔ),看出百年來南方大地的變化。我覺得無論現(xiàn)在時代怎麼變,那種好的、善良的傳統(tǒng)文化都會傳承下來的,只有這個東西,使我們精神更加豐富。
瀟湘晨報:您在鄉(xiāng)村待了八年,但鄉(xiāng)村並不是你居住最長的地方,為什麼作品更多寫的是鄉(xiāng)村?
陶少鴻:精神聯(lián)繫還是鄉(xiāng)村更牢固一些,畢竟是少年時候在鄉(xiāng)下待了八年,印象實(shí)在太深刻了,對我影響也是最大的。鄉(xiāng)村生活于我來説,最大的獲益是有了最真切的生命體驗,感受到了人與大自然最緊密的聯(lián)繫。站在泥香四溢的土地上,你可以聽見萬物生長的聲音,看到四季輪迴變幻的色彩,你會感到你與大自然融合在一起,你就是它的一份子;置身鄉(xiāng)村生活中,你必須親手種植莊稼養(yǎng)活自己,並因此而體悟生活之艱難,生命之堅韌。總之一切體驗都會讓你感到人生既憂傷又美好。這其中就會有審美意識自然天成,它不知不覺地滲入到你的心靈中,進(jìn)而影響到你後來的生活與寫作。鄉(xiāng)村生活是艱苦的,卻又是詩意的,我想這就是所謂的鄉(xiāng)土題材吸引我的原因吧。我寫過各種題材的小説,但很大一部分是寫鄉(xiāng)村生活的,其緣由不光是熟悉那裏的世俗人情,我想主要還是因為有種割不斷的精神聯(lián)繫吧。故鄉(xiāng)永遠(yuǎn)是你的精神胎盤,無論你走到何處,都有條看不見割不斷的臍帶與之相連。(文/趙穎慧)
[責(zé)任編輯:楊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