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追尋《富春山居圖》論辯之路——對(duì)話樓秋華

《中國(guó)美術(shù)報(bào)》第229期 美術(shù)副刊
【編者按】2011年6月1日,“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在臺(tái)北開幕,展覽中分藏于浙江和臺(tái)灣的“剩山圖”與“無(wú)用師卷”圓合,成為全球華人備受矚目的重大事件。今年恰逢展覽舉辦十週年,多位學(xué)者發(fā)文論述樓秋華著作《〈富春山居圖〉真?zhèn)巍罚ㄐ抻啽荆瑯乔锶A在本文中重溫了當(dāng)年新書從初版到修訂本的過(guò)程以及《富春山居圖》研究背後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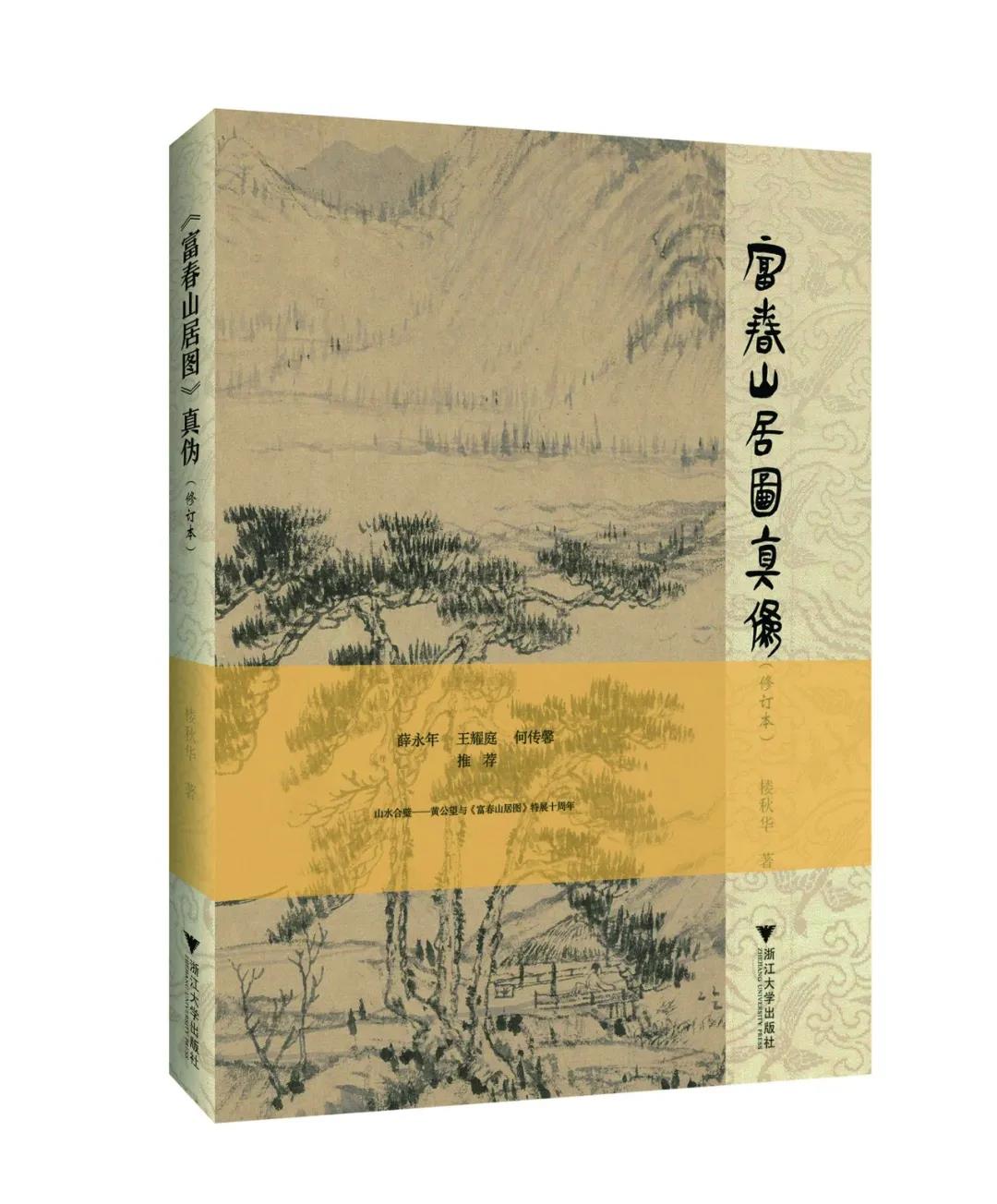
《〈富春山居圖〉真?zhèn)巍罚ㄐ抻啽荆?/font>
作 者:樓秋華
出版社: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
問(wèn):今年是兩岸“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十週年,一些專業(yè)媒體相繼發(fā)表著名學(xué)者王耀庭、何傳馨諸先生的書評(píng),對(duì)您的著作《<富春山居圖>真?zhèn)巍罚ㄐ抻啽荆┳隽司?dāng)?shù)恼撌觯绕涫呛蝹鬈霸谖恼轮刑峒澳闹鲗?duì)當(dāng)年合璧特展的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您可否就此做一回顧?
樓秋華:非常感謝臺(tái)北“故宮博物院”的兩位先生。何傳馨先生是當(dāng)年合璧展的策展人,了解《富春山居圖》的研究狀況。令我驚訝的是,十年過(guò)去了,他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過(guò)程和細(xì)節(jié)還記得那樣清楚,更沒(méi)想到會(huì)將這些經(jīng)過(guò)寫入書評(píng),令人既慚愧又感佩。回想起來(lái),2010年秋拙著出版不久,時(shí)任臺(tái)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zhǎng)的馮明珠獲悉後,專程到富春江畔過(guò)訪于我,相談甚歡,後來(lái)又因合璧展學(xué)術(shù)專題向我約稿。此後,臺(tái)北“故宮博物院”邀請(qǐng)我前往做專題講座。當(dāng)中,我與政府代表團(tuán)成員一道出席了合璧展的開幕式。在現(xiàn)場(chǎng)感受到兩岸山水合璧特展引發(fā)全球矚目的巨大影響力,印象非常深刻。另外,2019年底至2020年初夏,我完成了《富春山居圖》全臨本,力圖追溯這一名卷火殉前的原貌,這是我長(zhǎng)期以來(lái)的一個(gè)心願(yuàn)。何傳馨先生也作了簡(jiǎn)要評(píng)論。
在兩岸“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十週年之際,拙著再次印行。於此,特別感謝海峽兩岸藝術(shù)史學(xué)者薛永年、王耀庭與何傳馨等諸位前輩的有力推薦。
問(wèn):您長(zhǎng)期關(guān)注《富春山居圖》,能簡(jiǎn)單介紹一下這一專題研究的起因與過(guò)程嗎?
樓秋華:對(duì)於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多年來(lái)我一直加以關(guān)注。記得1999年春天,我應(yīng)西泠印社諸君之邀著手編著《趙孟頫畫語(yǔ)錄圖釋》。當(dāng)時(shí)初稿甫成,請(qǐng)王伯敏先生過(guò)目,王老先生和藹地對(duì)我講,你是富陽(yáng)人,還可以研究一下黃公望,他是趙孟頫的弟子,尤其是《富春山居圖》這件傳世名作,意義重大。我告訴王老,西泠印社出版社是有“黃公望畫語(yǔ)錄圖釋”這個(gè)選題的,也曾建議我執(zhí)筆編著,只是覺(jué)得黃公望傳世作品太少,難以與其《寫山水訣》等做一對(duì)應(yīng)的圖釋。王老表示,確實(shí)有這個(gè)局限。後來(lái)我把王老先生的一些説法轉(zhuǎn)述給富陽(yáng)相關(guān)人士,得到了重視。
令人關(guān)注的是,當(dāng)時(shí)媒體上連續(xù)發(fā)表了多篇文章,內(nèi)容大體涉及《富春山居圖》真?zhèn)螁?wèn)題。更令人訝異的是,當(dāng)時(shí)出版社正推出歷代名畫解析,其中就包括《富春山居圖》,可見一方面是真?zhèn)握撧q的主角,一方面則作為傳世經(jīng)典。
之後的十年間,我一直陸陸續(xù)續(xù)進(jìn)行梳理與研究,但是受制于個(gè)人學(xué)識(shí)以及客觀條件,進(jìn)展緩慢。一直到2007至2008年間,形成了約三四萬(wàn)字的綜述,評(píng)騭各家得失之外,還包括了個(gè)人的初步考述。好友高士明看了之後,建議再做些擴(kuò)展。不久,得到了故宮博物院藏品的一些圖像,進(jìn)展加快。尤其是在鮑賢倫老師幫助之下,獲取了多家機(jī)構(gòu)藏品的相關(guān)圖像,使得這一研究在2010年1月基本完成。由於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的重視,加上這一年春天的機(jī)緣巧合,本書初版在是年秋天面世。
問(wèn):當(dāng)時(shí),兩岸掀起研究這一名作的熱潮,您的著作也産生了較大影響。這次的修訂本與初版本比較而言,主要有哪些區(qū)別?
樓秋華:應(yīng)該説,本書修訂本與初版時(shí)的主體內(nèi)容一致,當(dāng)然也增加了個(gè)別章節(jié)。這是基於近十年來(lái)新的研究資料的相繼出現(xiàn),我對(duì)於相關(guān)論題做了進(jìn)一步考述,陸續(xù)發(fā)表了一些文章,這些新內(nèi)容大約佔(zhàn)全書的三分之一。此外,開本大了些,書中圖像較之前有了更好的底本。尤其是圖像的獲取,對(duì)於大多數(shù)研究者而言,多少存在一定困難,有些作品難得一見。
問(wèn):對(duì)一件作品的研究最終寫成了一本書,這當(dāng)然與這件名作本身的複雜性有關(guān)。同時(shí)也應(yīng)該與您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理念直接相關(guān),您覺(jué)得主要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
樓秋華:簡(jiǎn)而言之,這可能涉及到語(yǔ)境重建。譬如,過(guò)往研究者對(duì)乾隆皇帝當(dāng)年鑒別之誤,往往一筆帶過(guò),甚至只是以嘲笑的口吻來(lái)評(píng)判其能力與心態(tài)。不過(guò),在我的研究中,雖也指出了他貴為天子,擁有至高無(wú)上的權(quán)力,一言九鼎、不容質(zhì)疑等等,但這僅僅是一個(gè)方面。另一方面,乾隆皇帝在十年、十一年(1745、1746)相繼收得“子明本”“無(wú)用師本”時(shí),畢竟只有三十五六歲,而且還是一位日理萬(wàn)機(jī)的皇帝,他對(duì)一件作品的真?zhèn)舞b別能力自然無(wú)法與專門鑒家相提並論。事實(shí)上,他在收得“無(wú)用師本”當(dāng)晚便陷入不解之謎團(tuán)。第二天,在大臣們的應(yīng)和聲中匆匆下了結(jié)論,並且認(rèn)為“子明本”前隔水處董其昌一跋為真。其實(shí),乾隆皇帝當(dāng)時(shí)熱衷於章草,而非董氏行楷書。鑒別時(shí)也沒(méi)有與內(nèi)府所藏的董其昌真跡相對(duì)照,整個(gè)過(guò)程比較隨意。如果他充分了解董其昌這一時(shí)期的典型書風(fēng),恐怕就不會(huì)做出這樣的判斷。本書中,我將董其昌在1596年前後所作的數(shù)件題跋也納入其中,有助於觀者加以比較、鑒別。當(dāng)然,這一切的前提乃是得益於目前發(fā)達(dá)而有效的圖像傳播。
進(jìn)而論之,乾隆皇帝在認(rèn)定“子明本”為真跡,並加以題跋、讚嘆時(shí),其實(shí)並無(wú)多少鑒別力。況且到了清中期,黃公望傳世作品已經(jīng)少之又少,即便作為皇帝,也只是有所耳聞罷了,並無(wú)機(jī)緣可以借鑒比較,他身邊的大臣更是如此。所以,當(dāng)乾隆皇帝收得“無(wú)用師本”時(shí),由於之前他在“子明本”上一跋再跋,“白紙黑字”,使他失去了迴旋的餘地,難以自圓其説。值得注意的是,《石渠寶笈》初編與續(xù)編均未著錄這件“無(wú)用師本”。
問(wèn):這麼説來(lái),“無(wú)用師本”並沒(méi)有像乾隆皇帝所説的“俟續(xù)入《石渠寶笈》”。
樓秋華:對(duì),確實(shí)如此。《石渠寶笈初編》在1748至1749年之間加了一個(gè)附錄,其中收錄了“子明本”,但沒(méi)有“無(wú)用師本”。編纂于1791至1793年間的《石渠寶笈續(xù)編》,也同樣沒(méi)有收錄“無(wú)用師本”。這顯然與乾隆皇帝當(dāng)初在卷首的説法相背離,可見他一直在回避這個(gè)問(wèn)題。其實(shí)這個(gè)難題,直至乾隆皇帝去世16年之後才得以“解決”。到了嘉慶年間,在1815至1816年編纂《石渠寶笈三編》時(shí),“無(wú)用師本”方才予以著錄。但相關(guān)文字仍然恪守政治倫理與君臣綱常,回避了真?zhèn)握撧q。所以我在本書中,專門增加了這一章節(jié),加以述及。
問(wèn):《富春山居圖》被譽(yù)為畫中之《蘭亭》,在畫史上究竟産生了多大的影響力,能否做一個(gè)簡(jiǎn)要的介紹?
樓秋華:應(yīng)該説,《富春山居圖》在雍正朝以前,基本上為今天所稱的江浙滬三地的名畫家與大藏家所珍藏。從明中期至清早期約200餘年間,逐漸成為人們爭(zhēng)相臨倣的經(jīng)典之作,尤其是沈周、董其昌、藍(lán)瑛、查士標(biāo)、王翚、王原祁等人一倣再倣,成為一種風(fēng)氣,影響廣大。
然而,隨著這一名卷在乾隆朝進(jìn)入清宮之後,世人難得一見真容,民間只有一些倣本以及偽本流傳,包括《富春山居圖》在內(nèi)的一大批名作的影響力漸漸消褪,似乎也未曾出現(xiàn)值得一提的臨倣本。與此同時(shí),山水畫名家也乏善可陳。這其中的相互關(guān)係,實(shí)在是藝術(shù)史研究中一個(gè)值得關(guān)注的重要話題。一直到民國(guó)之後,《富春山居圖》重見天日,以多種方式出現(xiàn)在公眾面前,逐漸恢復(fù)其應(yīng)有的藝術(shù)生命力。
問(wèn):您在書中,以大篇幅對(duì)“子明本”與“張宏本”關(guān)係做了考辨,這似乎在其他地方未曾見到,您是如何打通這一路徑的?
樓秋華:以往研究中(或者包括當(dāng)下),“張宏本”除了徐邦達(dá)先生的文章作為《富春山居圖》臨倣本之一加以羅列之外,確實(shí)也少有人論及。所以我在2010年的初版提出了“張宏本”與“子明本”密切關(guān)係之後,引起了一些學(xué)者的注意,因?yàn)檫@不僅關(guān)係到“子明本”的真相,也涉及不同的作偽方式。
我是畫山水畫的,對(duì)畫面筆墨與章法的細(xì)節(jié)相對(duì)比較敏感,經(jīng)過(guò)再三地逐一比較,最終提出個(gè)人看法,後在文章中對(duì)於“子明本”與“張宏本”的摹倣(作偽)途徑、材質(zhì)特性等做了進(jìn)一步探討。
在本次出版的書中,加入了一件款署“辛卯中秋前二日”鄒之麟名下的橫卷,這同樣也是過(guò)往研究中幾乎無(wú)人觸及的,從而對(duì)另一卷鄒之麟名下款署“辛卯冬日”的臨倣本再次做出回應(yīng)。要知道後者在上世紀(jì)70年代《富春山居圖》真?zhèn)握撧q與原貌的追溯中,曾經(jīng)産生過(guò)非常重要的影響,無(wú)法回避。
問(wèn):過(guò)去有些研究對(duì)《剩山圖》的真?zhèn)慰捶ㄝ^多,您這裡是否有新的論述?
樓秋華:1650年,《富春山居圖》因火殉事件而分為兩段。其中卷首的《剩山圖》如今藏在浙江省博物館,長(zhǎng)度為51.4釐米,約為臺(tái)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後大段“無(wú)用師本”(636.9釐米)的十二分之一,見到的機(jī)會(huì)相對(duì)比較多。在“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期間,相關(guān)文獻(xiàn)將《剩山圖》引首“富春一角”的題寫者誤識(shí)為“韓對(duì)(對(duì))”,不詳其人,而輕輕略過(guò)。因此,《剩山圖》在康熙朝之後直到晚清約200年間的收藏脈絡(luò)存在空白,成為遭人質(zhì)疑的原因之一。其實(shí)題寫者為活動(dòng)於乾隆、嘉慶、道光年間的韓崶(1758—1834),他是一位比較重要的官員,生平也較為清晰。就其書風(fēng)而言,“富春一角”大約是他五六十歲時(shí)所書,這就為《剩山圖》的流傳史補(bǔ)上重要一環(huán),我在本書中對(duì)此有所提及。當(dāng)年七人鑒定小組的正確辨識(shí),似乎知者寥寥。
問(wèn):您前面提到從1999年起,便一直關(guān)注、研究《富春山居圖》真?zhèn)危两褚颜?0年。將來(lái)還會(huì)繼續(xù)這一領(lǐng)域的研究嗎?
樓秋華:這20年中,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我生活的重要內(nèi)容,時(shí)至今日,大致可以告一段落。事實(shí)上,我還做了一些其他的相關(guān)研究,譬如在2012年春天完成對(duì)《蘭亭集序》“創(chuàng)作真相”的初步考論。我想不久的將來(lái),還會(huì)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邊創(chuàng)作邊研究,繼續(xù)盡個(gè)人的綿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