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一度看櫻花
不多久,一年一度櫻花盛開的季節(jié)就要到來。櫻花在中、日兩國都是著名的觀賞花卉,在日本尤盛。每當(dāng)櫻花即將盛開之際,日本各地都會在櫻樹種植的道路兩旁,用醒目的指示標(biāo)記在地上劃分好場地,屆時供市民賞花之用。由於公共資源有限,使用全憑先來後到,在那些著名的賞櫻景點(diǎn),花意最濃的枝頭底下,往往可見卷著鋪蓋被褥,地墊睡袋一應(yīng)俱全的“佔(zhàn)位者”。他們或者是家族、好友輪流,或是由企業(yè)、社團(tuán)委派,從櫻花含苞開始就來站崗,只為花朵綻放的那幾天,能和家人、好友、同事,在落英繽紛之中,和滿街席地的賞花人們一道,享受清酒美食,與自然融為一體。
然而,就是這日本詩人本居宣長所吟咏的“如果問什麼是寶島的大和心?那就是旭日中飄香的山櫻花!”給現(xiàn)代的東亞社會帶來了深刻的記憶。“從明治時期開始,各界政府從視覺和概念上均把軍事行動和軍人的陣亡美學(xué)化了。櫻花的形象被大量利用……代表日本精神的櫻樹,在帝國擴(kuò)張時期遍植它的殖民地,目的是把殖民地空間轉(zhuǎn)換為日本的空間。”“櫻花美學(xué)的動員在實(shí)施神風(fēng)特攻隊(duì)行動時達(dá)到了高潮。粉紅色櫻花被畫在特攻隊(duì)?wèi)?zhàn)機(jī)兩側(cè)的白色背景上,日語關(guān)於櫻花的各種詞語都被用來稱謂這支特種兵。”
櫻花作為一種美麗、爛漫的花朵,本是出於與世無爭的自然之物。卻因?yàn)轭l頻出現(xiàn)于日本的軍徽、機(jī)身,無端成為了日本軍國主義、殖民擴(kuò)張的一部分,使東亞人民望見櫻花,或許會産生一種不快的記憶。這對櫻花本身是否稱得上一種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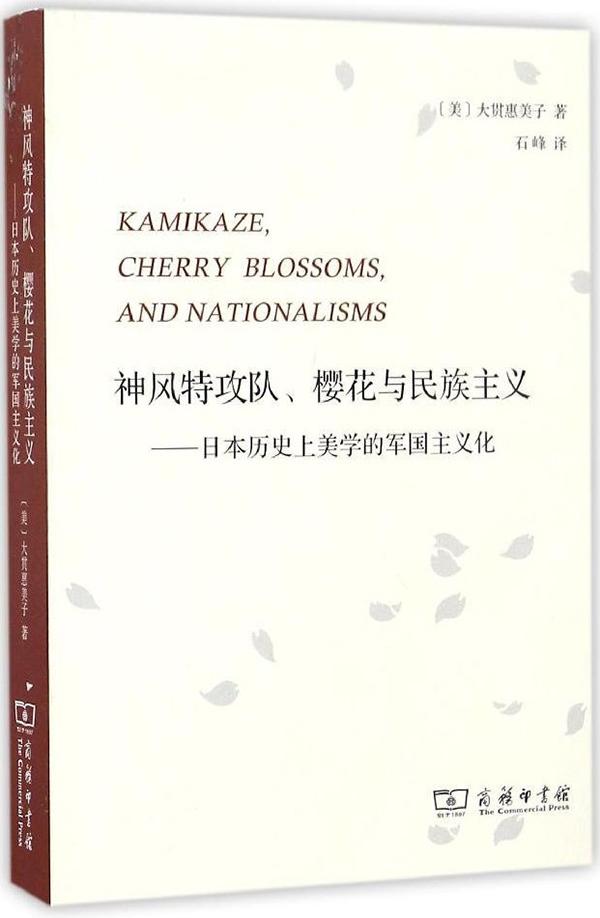
《神風(fēng)特攻隊(duì)、櫻花與民族主義——日本歷史上美學(xué)的軍國主義化》, (美)大貫惠美子 著,石峰 譯,商務(wù)印書館,2016年10月。
櫻花是如何與日本軍國主義聯(lián)繫在一起,並被借用為日本對外軍事擴(kuò)張的象徵?這裡有著怎麼樣曲折的過程?一位美國人類學(xué)家不願令其蒙受不白之冤,決定為櫻花一辯。美國威斯康星大學(xué)麥迪遜分校人類學(xué)教授、日裔美國學(xué)者大貫惠美子在《神風(fēng)特攻隊(duì)、櫻花與民族主義——日本歷史上美學(xué)的軍國主義化》(以下簡稱《櫻花》)中,為我們展現(xiàn)了櫻花與眾不同的身世。

大貫惠美子
從古至今話櫻花
“在古代日本最神聖的植物是稻米。稻穗居住著神的靈魂,體現(xiàn)為谷粒,因此稻米代表了農(nóng)業(yè)生産力。櫻花的象徵等同於稻米。因?yàn)檫@樣的等同,所以也是維持生命能量的象徵。”大貫惠美子一開始就引用日本民俗學(xué)創(chuàng)始人柳田國男對稻米的敘述,把櫻花的地位提到和稻米等同的地位。
然而,這樣一種重要的櫻花,在日本早期文學(xué)、美學(xué)的範(fàn)疇中是缺失的。通過對櫻花早期形象的討論發(fā)現(xiàn),在日本早期詩集《萬葉集》收錄的四千五百十六首詩歌中,有四十七首出現(xiàn)了櫻花,而這只佔(zhàn)到所有詩歌總數(shù)的百分之一的櫻花詩“被男詩人當(dāng)作愛情和婦女的象徵”。由此可見,“在這部詩集中櫻花並沒有佔(zhàn)據(jù)中心位置,主要是以荻和梅作為主題和隱喻”。櫻花僅僅作為婦女美麗的象徵,並不具有更超越的意義。
而且,櫻花甚至梅花在日本文化中的核心地位,還受到中國文化傳入的菊花文化的衝擊。“平安時期,中國的重陽節(jié)賞菊傳入日本。天皇在賞菊時,就用帶著露水的菊花的花心‘菊棉’擦拭身體”,與之相伴的,還有漢詩的朗誦。菊花在日本文化的重要象徵含義,一直延續(xù)至今,無怪乎大貫惠美子的前輩魯思 本尼迪克特用《菊與刀》(卻非櫻花)這組具有強(qiáng)烈對比的隱喻來概括了日本文化的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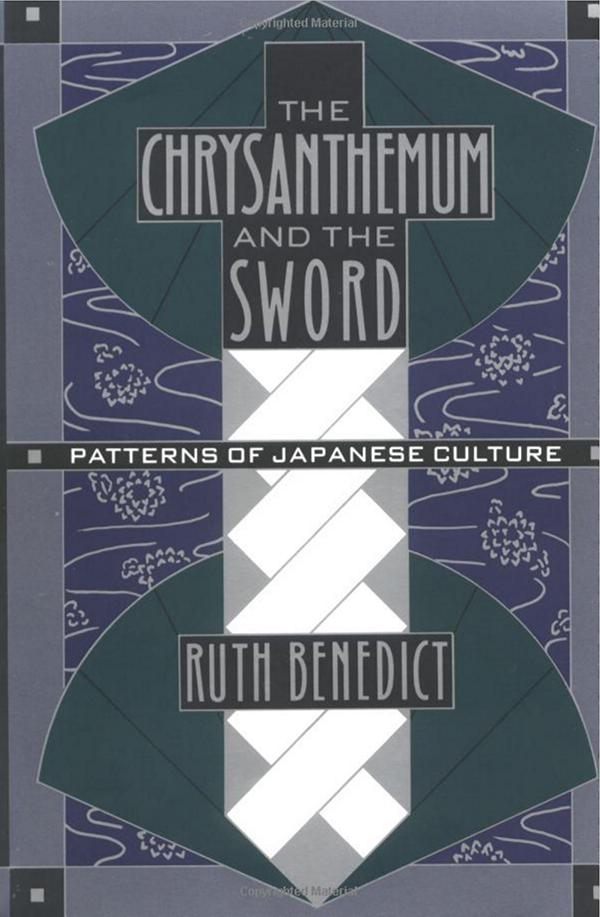
魯思 本尼迪克特:《菊與刀:日本文化的類型》
按照大貫的考察,櫻花在日本的崛起,可以追溯到相對較晚的江戶時代。德川家的幕府將軍不但自己種植櫻樹,還建立了每年讓各地藩主前往江戶居住(據(jù)稱,為防止藩主在領(lǐng)地造反)的制度,使得藩主將各自領(lǐng)地的櫻花品種帶到都城栽種。這一舉措,使江戶一舉成為了“櫻花之國”,在當(dāng)時“江戶百景”中,有“二十一個名勝因其櫻花的美麗而被選中。梅花僅出現(xiàn)四次”。從這以後,櫻花作為日本人的集體象徵,開始從自然景致,向文學(xué)表達(dá),進(jìn)一步向著精神層面逐步發(fā)展起來。而在此時,櫻花的主要含義,還僅僅是用櫻花盛開時,濃密滿枝頭的花朵,代表人們?nèi)粘V兴鶉煌耐⒌纳Α⒎敝沉Γ@種樸素的意象,尚未被後來更狹隘的觀念渲染。
可以看到,直到此時,櫻花作為一種日本常見的植物,雖然開始繁盛地種植遍野,但還缺少一個契機(jī),將其提煉為一種具有特殊象徵含義的符號。而這個契機(jī)就來自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的木戶孝允,在他的主持下東京招魂社(後來的靖國神社)開始種植櫻花,“目的是讓美麗的櫻花去安慰那些陣亡的武士”,儘管“這個計(jì)劃並不包含鼓勵軍人犧牲自己的生命”。 東京招魂社建立的最初目的是為了紀(jì)念在“壬辰戰(zhàn)爭”中,為了擊敗幕府軍隊(duì)而犧牲的維新派士兵。這與後來陸續(xù)移入神社供奉的日本歷次對外戰(zhàn)爭中的亡者有著本質(zhì)區(qū)別,然而,當(dāng)櫻花與這個戰(zhàn)爭龐然大物産生了交集,它的象徵含義也隨之向著更大,也更無序的方向延伸開去。
明治維新後,新制的日軍海軍、陸軍制服中都出現(xiàn)了櫻花。而軍人的陣亡,則被隱喻為櫻花的凋零。正如明治後日本教育家新渡戶稻造在《武士道》中對櫻花與武士道所作的比擬,他談到“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徵櫻花一樣,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而將軍人履行武士道的自殺,比喻成“‘剎那寂滅’的櫻花,在日本國民心裏象徵著格外美麗的死亡”。對此大貫認(rèn)為,“在現(xiàn)代軍國主義意識形態(tài)中,最明顯的相似之處是櫻花結(jié)果之前飄落和年輕軍人結(jié)婚生子之前陣亡。兩者都被剝奪了生殖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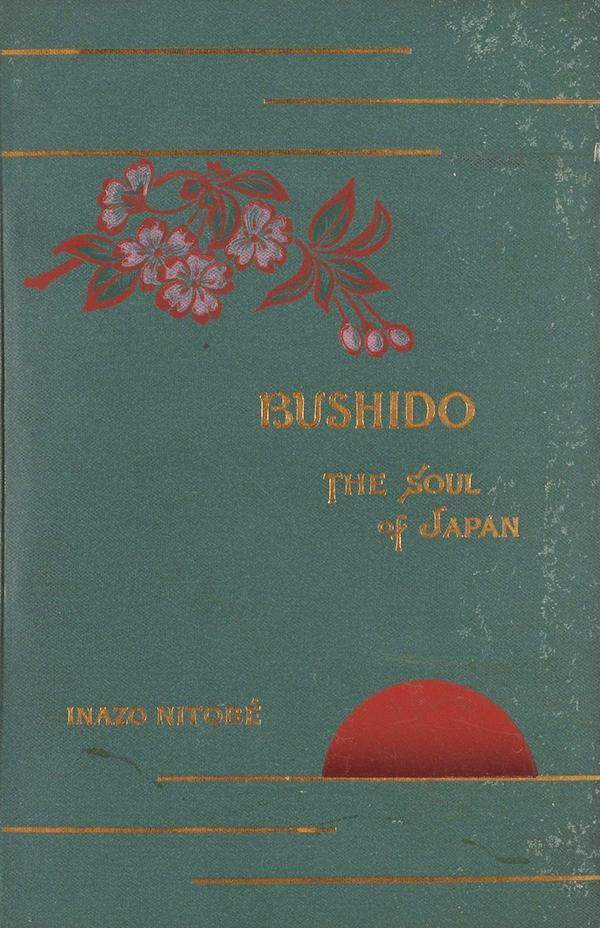
新渡戶稻造:《武士道——日本的靈魂》(1900)
“櫻花的象徵意義從象徵生命力的盛開的櫻花轉(zhuǎn)化到了象徵軍人陣亡的落櫻。”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擴(kuò)張,這種象徵也隨著日本軍隊(duì)向外延伸。這或許是櫻花本身的含義在近代以來經(jīng)歷的最大轉(zhuǎn)變,也最終造成了現(xiàn)代東亞社會對櫻花形成的最大誤解。
櫻花:一種發(fā)明的傳統(tǒng)?
為了檢驗(yàn)大貫惠美子對櫻花形象變遷歷程的探索,我特地檢索了柳田國男關(guān)於日本歷史民俗的專著。一個不爭的事實(shí)是,不但在日本早期文獻(xiàn)中,甚至近代日本收集的民俗故事中,都沒有見到櫻花的出現(xiàn),連作為故事背景的線索也沒有找到。這不禁讓我懷疑起櫻花在日本的悠久歷史。同時對大貫早先出版的《作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時間的身份認(rèn)同》一書的考察,也證明櫻花與稻米之間的象徵含義似乎並未構(gòu)成明確的聯(lián)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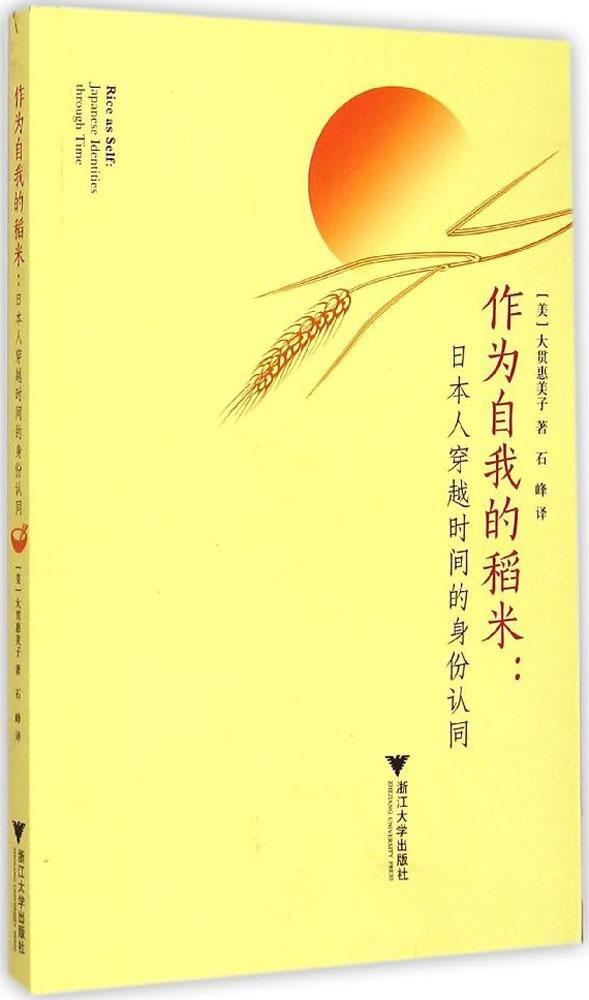
大貫惠美子:《作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時間的身份認(rèn)同》
我忍不住查閱了有關(guān)植物分類的一些資料,不出意料地發(fā)現(xiàn),櫻花的原産地是包括中國西南在內(nèi)的喜馬拉雅山脈。而且,中國西南地區(qū)至今仍生長著數(shù)量最豐富的野生櫻花品種。儘管很難證明日本的櫻花品種是否源自中國,但唐代李德裕《鴛鴦篇》中的“二月草菲菲,山櫻花未稀”,以及李商隱的《無題》中的“何處哀箏隨急管,櫻花永巷垂楊岸”或許表明,源自唐代中國的賞櫻傳統(tǒng),也隨著日本遣唐使一道,進(jìn)入了平安朝的日本。只是當(dāng)時日本本土櫻花並未普及,難以形成如同賞菊一般的“共情”。
而直至江戶時代,由於幕府將軍偶然的推動,櫻花以其旺盛的生命力竟從百花叢中一枝獨(dú)起,成為都城江戶重要的自然景觀。隨著明治初期日本政局在西方文化迫近下急切發(fā)生的變化,日本社會急需重新審視自己的當(dāng)下與傳統(tǒng)的關(guān)係。“那些親近政府的人對櫻花的意義有不同的理解——一些人認(rèn)為其代表了封建日本,反之,另一些人則認(rèn)為象徵了現(xiàn)代新日本。”各種勢力,都呼喚著一種能代表新的歷史階段,又與過去保持聯(lián)繫的紐帶。他們仿佛巧合般地從櫻花這一寬泛又具體的“能指”中,達(dá)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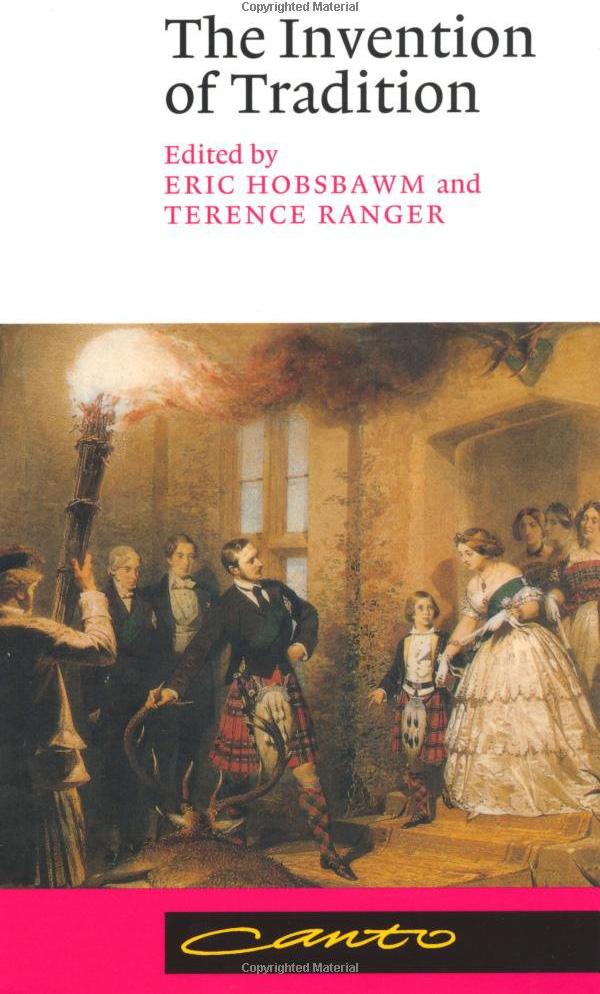
E. 霍布斯鮑姆,T. 蘭傑編:《傳統(tǒng)的發(fā)明》
正如《傳統(tǒng)的發(fā)明》中,牛津大學(xué)歷史學(xué)家休·特雷弗-羅珀對蘇格蘭男性穿著——傳統(tǒng)格子呢短裙所作的分析那樣,“現(xiàn)在被視為蘇格蘭古代傳統(tǒng)之一的蘇格蘭褶裙很可能從未存在過”,而只是出自十八世紀(jì)末蘇格蘭高地社會對愛爾蘭文化的反抗。在這一文化變革時刻,蘇格蘭知識分子精心創(chuàng)造了一個想像的凱爾特時期,為這一偉大傳統(tǒng)提供證據(jù)的,則是臨時創(chuàng)造出來的格子呢褶裙,還有風(fēng)琴。歷史學(xué)家霍布斯鮑姆將這種晚近出現(xiàn)的“古老”傳統(tǒng),稱之為“傳統(tǒng)的發(fā)明”。
於是,櫻花,這一過去並未被賦予如此重任的植物,就在這一變革時刻,被各種妥協(xié)的力量創(chuàng)造了出來,成為了新渡戶稻造筆下一種全新的古老象徵:“櫻花自古以來就是我國國民所喜愛的花,是我國國民性的象徵。”只不過,這個“自古”或許並不太古老。

1984年到2004年五千日元日本銀行券的新渡戶稻造。
歷史歸歷史,自然歸自然
櫻花,及其背後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是不是一個類似的“傳統(tǒng)的發(fā)明”,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至少,我們從大貫惠美子這裡,並沒有找到更多有關(guān)櫻花的早期證據(jù)來證明其在日本的悠久歷史。正相反,我們看到的更多是,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在尋找自身在世界格局中的定位時,有意將自己過去來自中國傳統(tǒng)(比如賞菊)分割開來,尋求一種具有獨(dú)立性自我表徵的過程。或出於對本文化的崇敬之心,或純粹缺乏“他者的眼光”,大貫受困于櫻花的“自古”,失去了將其與當(dāng)代路徑勾連的創(chuàng)造性視野。
不過,她在《櫻花》中所提供的五個“神風(fēng)特攻隊(duì)”飛行員的事跡,卻從另一個層面揭示了櫻花游離于軍國主義之外的獨(dú)特一面。一個名叫林尹夫的神風(fēng)特攻隊(duì)飛行員的詩歌顯示,“他的愛國主義與‘為天皇和國家捐軀’儀式形態(tài)毫無丁點(diǎn)關(guān)聯(lián)。他對落櫻的想像和靖國神社也同樣沒有關(guān)聯(lián)”。他從未用櫻花想像自己與日本侵略戰(zhàn)爭的聯(lián)繫,他只是一個被戰(zhàn)爭裹挾的可憐的大學(xué)生,在這場毫無希望也缺乏正義感的戰(zhàn)爭中,不幸地淪為了可悲的祭品。他唯一和櫻花相似的,就是用短暫的生命追隨了落櫻不染的純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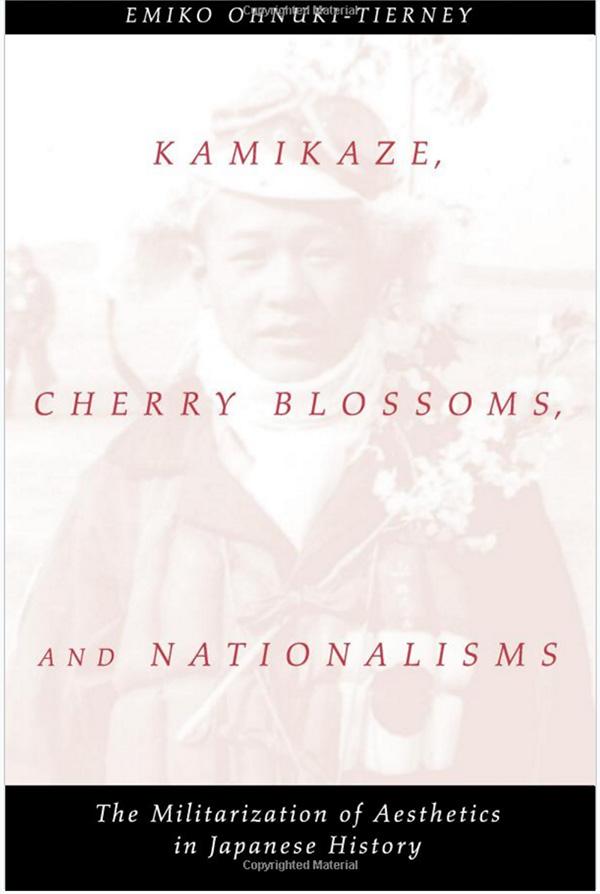
《神風(fēng)特攻隊(duì)、櫻花與民族主義》英文版
透過《櫻花》一書,大貫惠美子展現(xiàn)了她的寫作意圖,通過展現(xiàn)“國家如何通過操縱日本歷史悠久的櫻花的象徵意義來説服人們,為天皇‘如美麗的飄零的櫻花’那樣死去是一種榮耀”,來反思戰(zhàn)爭機(jī)器對普通日本民眾的傷害——人們並非情願淪為戰(zhàn)爭的犧牲品,而只是被某種帶有象徵色彩的意識形態(tài)所驅(qū)動。
當(dāng)然,我們通過更多維度的視角(主要來自大貫本人提供的材料)可以發(fā)現(xiàn),普通日本民眾本身對櫻花這一“發(fā)明的傳統(tǒng)”似乎保持了理性距離。他們未必被櫻花的絢爛遮蔽了雙目,盲目地投身於戰(zhàn)爭的狂熱,他們更多地只是無法自外于日本軍國主義的槍炮,捲入了歷史的車輪。將他們等同於落櫻般墜落的盲從者,未必是種公允。
遑論她的努力是否成功,大貫惠美子至少用本書為櫻花提供了一種辯護(hù),將櫻花本身與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手段區(qū)分了開來。讓我們無論在中國公園,還是日本街頭、堤岸觀賞花團(tuán)錦簇的櫻花時,看到更多的是自然之美。還櫻花一個天然無邪的同時,也用這種無邪照見我們的當(dāng)下,始終對“發(fā)明的傳統(tǒng)”及其背後的脈絡(luò),保持一種清醒與理智。(文/張經(jīng)緯)
[責(zé)任編輯:楊永青]